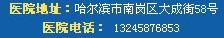《玉龙雪山记游》34×47cm年
一生好入名山游
年仲夏的一天,我与林一方兄清晨从罗浮山黄龙古观出发,沿着古蹬道上山,蹬道年久荒圮,有数处需要攀藤附葛而上,历大小石楼、玉鹅诸峰,午后抵达顶峰飞云顶。其时晴空万里,罗浮四百三十峰,历历在目,苍山如海,天风似浪,令人几欲凌虚飞去,身在此山之中,并无不识罗浮真面之憾,反有千峰入袖之感。下山后发兴填了一首词《忆少年·登罗浮山飞云顶》:“淙淙泉水,悠悠古径,蒙蒙云岫。骑鲸过巨浪,绝尘摩星斗。始信山君终可就,倩麻姑、奉觞称寿。虽霜鬓如此,却千峰入袖。”近日,许晓生兄帮忙张罗一个山水画展,我便用“千峰入袖”四字作为画展题目了,也是记录下多年来游历山水的一份心情。
“一生好入名山游”,林泉高致,对于中国传统文人来说,是一份割舍不了的情感,古人把这份情感雅称为“烟霞癖”。我年轻时,有过许多爱好,比如足球、围棋。中岁以还,尽皆淡去,唯独游历山水的爱好与日俱增。不过,与现在年轻人的探险不同,我只去有人文景观的山水,对于异域风情与险绝之处,不太感兴趣。这也是传统的观念——可行可望,终不如可游可居。
《信号山远眺》46cm×35cm年
近年因为学术交流,我获得许多到外地出差的机会,每至一地,只要条件许可,都会去当地名山一行。白天如无暇,便在晚上赏夜山。记得几年前南京艺术学院李安源兄邀我至南京讲学。讲座结束,回宾馆路上,抬头望见皓月当空,如此良夜,岂可辜负,于是发念至东郊紫金山一行。车停于山脚下,我独自踏着碎石铺成的山径逶迤而上,山径没有路灯,月光从林间树杪透过,在石径上留下斑驳的影子,偶尔会有一二山客走下山来,“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”,于是摸索着一直走到山路尽头天文台。正当凭栏远眺秣陵山水,畅怀得意之时,忽得安源兄电话,原来是帮我订车的学生向他报告,车子没回宾馆,而是偏航到了紫金山。他怕出意外,急忙来电问讯。得知情况后,他不觉失笑道:“若公豪兴不浅。”安源兄实不知我有好几年住在广州北郊白云山下,每晚策杖入山行数里,故不惧夜行山路也。
《白堤冬日》34×47cm年
至于说到豪兴不浅,倒有一事可足一记。大约二十年前我在杭州念书,有一次独游西湖,突逢暴雨,未带雨具,衣衫鞋袜尽湿,于是索性把脚上的北京老布鞋脱去,在斜风细雨中跣足而行,从孤山一直走到断桥。雨中游人稀少,遥岑远目,如仙子披羽衣立于水际,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。东南妩媚,雌了男儿,紫翠湖山,诚非虚言。我游西湖不下数十次,独以此次最得山水之趣,也最难以忘怀。
山水之美,摄人心魄,其实是很难用文字、绘画来表达的,或许最好的表达方式就像《世说新语》中的人物那样“辄呼奈何”,不立文字而自有一片深情在焉。然而我于游山之余,终不免技痒,于是濡墨铺纸,点染几笔,既是纪录游屐所及,也算是抒发一下思古之幽情吧。十多年下来,也就积累了些许画作,现在挑了部分出来,以求方家教正。最后需要说明的是,我的主业是中国书画史研究,但用于山水画实践上的时间其实也不少,之所以能坚持临池不辍,正在于这种对山水传统的温情与敬意,自然还有那无法自拔的“烟霞癖”。(辛丑秋日李若晴于粤垣投笔斋)
《远眺玉龙雪山》45cm×63cm年
文人意趣兴感每殊
——若晴兄的山水诗与画
日前读若晴兄《投笔斋诗词稿》,姿度倜傥,大可把玩良怡。若兄诗大抵以渊雅真挚为主,诗学似取法宋人宛陵、山谷、东坡、放翁、诚斋诸贤为宗,仿佛间又见近人陈散原“同光”意趣,笔下文人感兴,清欢可寻。
若兄诗法前人,更重于心性。晚明李日华《六砚斋笔记》曾云:“凡状物者,得其形不若得其势,得其势不若得其韵,得其韵不若得其性。”纵观若兄诗中兴味,实肖古人心性,无论于学问之专,登临之趣,待友之诚,一一可细辩于诗笺中。余尤爱其山水诗,优游林下,未失天然,真正践行古人林泉雅道,因其多画山水之故,其诗博肆之余,益见情景蕴籍气息,故其画笔幽胜处,亦多于诗境中厮磨而成。
甲午深秋,余与若兄诸友曾有波罗神庙之游。岭南秋老,日光晻霭,徘徊庙中,楼殿巍闳。庙左高垣有亭翼然,名为“浴日”,吾等登陟山石,亭台探幽,形胜沾润,胸次甚快,若兄最为敏博,不久吟句成《重阳登浴日亭步东坡韵》:“人世几回变换天,浴亭依旧近黄湾。桑田也信经沧海,碑碣低吟怅岘山。落魄东坡悲白发,负暄新会献龙颜。二公日月争光处,不在朝堂在水间。”当日客中匆匆无暇一和,以为重阳达意而已。弹指之间已多年过去,今日重读,如遇故人,不觉神驰,时日逝水,故人无恙否?斯景无恙否?其情无恙否?兴感每殊,百端交集。(陈俊宇辛丑芒种于滋兰斋)
《悬空寺记游》34×47cm年
忆旧探新:读李若晴《西泠纪游》系列组画
辛丑夏夜,若晴师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abmjc.com/zcmbyf/9178.html